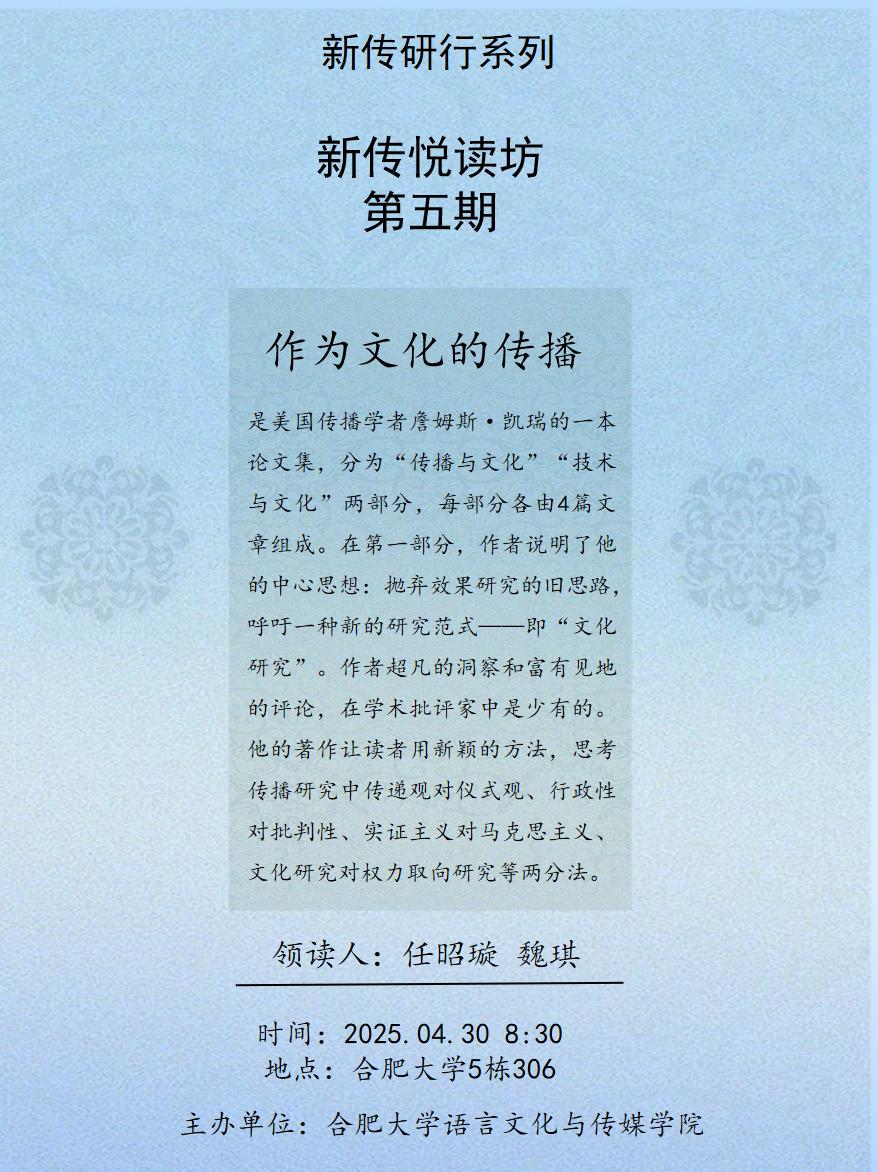
作者:詹姆斯·凯瑞
报告人:魏琪、任昭璇,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2024级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
一、 引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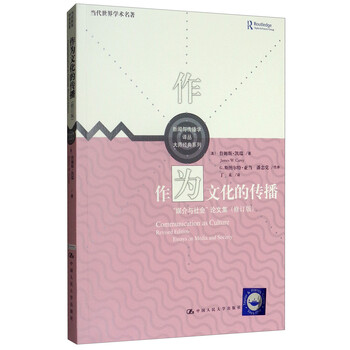
该书分为两部分,即传播与文化和技术与文化。作者系统阐释了其传播观,并反对美国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,他认为应该将传播看成文化,声称自从其踏进传播领域,就发现传播学的主导研究范式是一种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。作者在该书中比较了传播研究中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之间的争论,认为争论本质涉及客观主义和主观表达的关系。
本书以文化研究为视角,重新审视传播的本质与社会功能,突破了传统传播学“信息传递工具”的功利框架,提出传播的核心是文化意义的构建与社会秩序的维系。通过对多学科理论的整合与历史案例分析,揭示了传播技术、文化实践与社会结构的深层互动关系。
二、 作者简介
詹姆斯·凯瑞(James W. Carey)(1934-2006)是媒介理论家、批评家,以及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。他曾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-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、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教授,并被誉为“美国本土的批判学者”。其著作有《作为文化的传播》《电视与新闻》《转变时代观念》。詹姆斯•凯瑞的传播学研究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,他的思想深受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,在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研究模式盛行的背景下,他提出传播“仪式观”,开辟了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途径。
三、 核心内容
(一) 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
杜威的传播观:杜威在《经验与自然》中提出“传播是最为奇妙的”,其“传递观”强调信息的有效传播与控制,而“仪式观”则更关注共享信仰和身份纽带。这两种观念在美国文化中相互影响,但学术界对“仪式观”的重视相对不足。
文化的重要性:尽管科学在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,但文化的意义并未因此被削弱。传播的“仪式观”反映了对有序社会文化的追求,如宗教活动中的集体仪式便体现了共同身份的纽带。
传播与文化的关系:通过比较“传递观”与“仪式观”,文章指出传播不仅是信息工具,更是文化深层意义的体现,强调了文化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。
(二) 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
通俗文化的争论:二战至朝鲜战争期间(1940s-1950s),美国学术界围绕通俗文化的性质展开激烈讨论。德怀特·麦克唐纳等保守派认为通俗艺术侵蚀传统文化,C·Wright Mills等左派则关注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。
传播学的局限:传统传播学研究忽视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,导致对艺术与社会生活的理解不足。例如,好莱坞电影的兴起被批评为商业化对艺术的侵蚀。
文化理论的发展:随着争论逐渐平息,焦点转向现代社会结构与权力统治,文化理论开始深入探讨传播的社会功能。
(三) 对“大众”和“媒介”的再思考
理查德·罗蒂的诠释学:罗蒂主张通过会话解放思想家,促进学者间的相互理解。他反对执着于普遍真理,而是提倡文明互动,形成新的社会联系。
电报的影响:电报作为19世纪的重要发明,扩大了人际传播范围,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形式。例如,电报使跨洲通信成为可能,促进了商业和政治领域的高效协作。
笛卡尔与维柯的立场:笛卡尔强调起点的偶然性,而维柯则关注表现主义的客观性,两者共同表明现实由人类行动造就。
(四) 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
知识的性质与目的:大众传播学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统框架的束缚,尤其是功利主义的解释模式。文章呼吁重新审视社会秩序与行为动机的联系。
文化研究的价值:文化研究方法能重新定义自我,关注媒介效果与功能的讨论,推动文化概念的深入理解。例如,韦伯的“文化科学”强调人类行为的主观性与社会结构的客观性。
未知领域的探索:文化研究的勇气在于追求未知领域,挑战现有研究方法的限制,以揭示真理与知识的不确定性。
(五) 电子革命的神话
桑顿·怀尔德的《第八日》:小说描绘了1900年庆祝世纪之交的场景,反映美国人对变化与希望的期待。“第八日”象征新纪元的到来,强调对未来充满信心。
电子技术的信仰:麦克卢汉认为电是人类的伟大施主,推动社会变革;布热津斯基则强调电子技术的转型使命,认为技术应实现民主与技术的兼容。
地方文化的侵蚀:尽管电子技术带来机遇,但也引发了地方文化的侵蚀问题,例如全球化语境下本土语言和传统的消逝。
(六) 空间、时间与传播手段
哈洛德·英尼斯的传播理论:英尼斯的著作《传播的偏向》《帝国与传播》展示了传播技术对空间与时间的深远影响,例如印刷术改变了知识保存方式。
反冷战立场:英尼斯不仅关注传播技术本身,还捍卫大学的传统,表达对冷战政策的批评态度。
北美文化的独特性:英尼斯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北美文化的独特性,强调学识与民族文化的关联。
(七) 未来的历史
F.L.Polak的未来观:Polak在《未来的幻象》中探讨了人类对未来的迷恋,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精确计时设备的兴起增强了预见能力。
乐观主义复兴:未来被视为进步、和平与民主的时代,公众通过对未来的激励抵制对过去的兴趣。例如,经济萧条时期人们仍对未来抱有希望。
虚假意识:南文斯指出,信仰的统一可能成为逃避现实问题的“虚假意识”。
(八)技术与意识形态:以电报为个案
亨利·亚当斯的自传:描述了18世纪波士顿与电报、铁路等科技进步的联系,标志着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工业化进程。
电报的变革:电报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,成为商业工具与思考工具。例如,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垄断了电报控制权,推动专利争端。
社会互动的变化:电报不仅影响传播与运输的关系,还重塑了社会互动与意识形态,成为科技进步的分水岭。
四、 研究范式创新
1、批判功利主义框架
呼吁超越“媒介效果”量化研究,关注传播如何通过文化实践建构社会现实(如韦伯强调行为主观性与结构客观性)。
2、倡导跨学科对话
罗蒂诠释学推动学者通过“会话”解放思维;笛卡尔与维柯哲学佐证“人类行动创造现实”。
3、坚持文化自主性
在科学主导的时代,重申文化对社会整合的核心价值(如电子时代仍需守护地方性知识)。
五、 启示与反思
本书预言了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:当算法媒介进一步延伸人类感官(麦克卢汉),我们更需警惕技术决定论的陷阱。追问:媒介全球化是否必然导致文化同质化?如何通过传播实践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?正如英尼斯对冷战政策的批判所示,传播研究必须保持对权力结构的警觉,方能在技术狂潮中守护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的主体性。
六、 结语
合上《作为文化的传播》,仿佛经历了一场关于“意义”本身的深刻对话。它有力地剥离了传播学长久以来披挂的“工具理性”外衣,将其内核“文化意义的创造与维系”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詹姆斯·凯瑞的洞见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理解传播的新维度:它不仅是信息的“传递”,更是社会得以凝聚、身份得以确认、现实得以构建的“仪式”。
编辑:魏琪、任昭璇
初审:刘露
复审:许婧
终审:查金萍